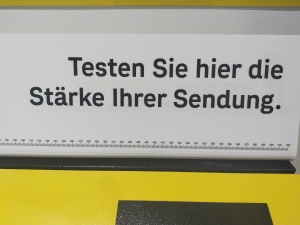《喊口号》
维马丁
如果说不能一面挺和平一面挺俄,是口号吗?应该怎么说话你才觉得可以?我觉得对我喊文革不对。你觉得我喊口号,还有人叫我红种,也许是你们长大在红肿时代。因为目前的战争,欧洲也有很猛烈的讨论,尤其是作家诗人们,比如在德国。德国笔会刚刚分裂,在柏林建立了新的笔会,就是因为有人觉得必须支持乌克兰,必须很快,其他都是次要的。我觉得他们对。另一方说德国和北约千万不能跟俄国直接打,这是最重要的。两方都不说俄国对,欧洲没有人觉得欧洲有理由开始打战,也许除了一些塞尔维亚人之外。欧洲近三十年是欧洲当代历史,中国人在中国没资格说出简单的判断。尤其是诗里就是很可笑。有时候倒有点道理,从外面看有可能看到里面看不到的。伊沙去过欧洲多次,自眼看到,还听到了些。
西方的逻辑
伊沙
那年去马其顿
出席斯特鲁加诗歌节
诗歌节的司机大哥
谈起该国的生存之道
彻底倒向西方
同时申请加入北约与欧盟
到现在
北约早早批了
欧盟迟迟不批
我想:西方的逻辑大概是
穷人入伙难
其家可架炮
2022.6.12
我当欧洲人一读就觉得有道理,哪怕最近跟伊沙吵架了多少。伊沙这首也许还有一点类似我从外面写中国出现疫情那一刻。
新型肺炎
维马丁
在中国
据说控制一切的人
那据说不可避免的一切的控制
又
失败了。
2020、2、10
CORONA-VIRUS
The people
in China
who are supposed to control everything
which is supposed to be inevitable
have failed
yet again.
MW February 2020
先写了中文,还有德语版。英语以后写的,也许第二天。这首在中国不能发表,网上能看到已经不错。这两年贴了几次,没有人说诗里的批评有什么不对。就是不能发表。同时候写了另一首可以发表的:
相信魔鬼
维马丁
恶性循环
用德语说
是魔鬼循环
所以说
新冠病毒
是魔鬼的错吧
2020、2
魔鬼循环,很多国家都有,疫情这几年都是魔鬼的时代。那么哪一首更重要?也许两种都是好诗,自己不好说。两种批评都很有用,这个可以自己说吗?第一首“据说”包括多年尤其在中国之外的媒体对中国社会的单独看法。
诗人对当代当面的社会问题反应不一定是直接的,也不一定需要很明显的反应,因为艺术需要以后也认得出来,大家都忘了当面细节以后,看到或听到作品就可以认出来某种情况,就是艺术的魔力。几百年,几千年以后还听得出来。不过具体情况也很重要,历史研究和艺术欣赏互相补助。说这些当外国人说也许不用,你们都知道,肯定有很多人说得更好。只是要认定,诗人有很多种。这就是伊沙推新世纪诗典的成功,纳入了那么多完全不同的声音。一开始还纳入了完全不属于任何跟伊沙有接触的圈子,了不起。新诗典是非常开放的东西。可惜这两年有一些很好的诗人不参加了,比如秦巴子,比如西安最出名的口语诗人们除了伊沙都不参加。非常可惜!不过也可以说,有了新诗典,持续了那么多年,做了那么多贡献,是一个非常大的,杰出到成立。大家的成立,还包括老外!
那为什么跟伊沙相处有时候很难?因为伊沙喜欢写政治。诗人有很多种,伊沙写诗也写很多完全不同的形体,同时候写梦,写鸟鸣,写日常生活,写自己家庭,写动物,写小区,写上课记录。所以不能说伊沙必须写政治,只是说长期免不了。不是每个人,每个诗人都这样,有的一辈子都写比较间接的,写得非常好。伊沙第一个代表作是1988年写的《车过黄河》。诗里有一个我隐身到厕所里,厕所里才有自己的时间、自己的地盘。这首诗讽刺一切伟大的期待,一切跟黄河、历史、伟人、民族联系的严肃的期待。伊沙可以讽刺一切,包括诗人自己。整个九十年代都这样,有很多杰出的代表作。新世纪也有不少讽刺自己的诗,也一直继续说到世界一切,说到中国和世界各种严肃的问题和现象。说到这儿都没有回答为什么跟伊沙相处有时候不容易。也许是脾气。跟我相处有时候不容易,就是因为脾气。还有其他的问题,但脾气肯定很明显。骂人很快,很厉害,很粗鲁。伊沙和我都有这个现象。一般看不到,否则哪有可能有了多年的友谊?哪有可能合作那么好?不只是我,如果伊沙脾气每天都这样,可以成功吗?新诗典可以成功吗?
四月份一首拙作说出了本来的问题。不是伊沙一个人,不是我一个人,不是中国或奥地利等等任何一个地方的单独的问题。
本来的问题
维马丁
疫情让本来的问题
显出来
特别清楚
战争让本来的问题
显出来
特别清楚
还要更快
本来的经济
本来的社会
本来的关系
老百姓
可以做什么?
需要
互相帮助,
这也显出来
特别清楚
其他还能做什么?
以前以为
本来的社会
本来的经济
本来的关系
一直会下去
不能阻挡
现在知道
并不这样
2022.4
写了以后在微信给湘莲子看,她马上说你怎么那么清楚说到了上海?写的时候我当然想到很多别的,完全没有具体想法写上海。那时候上海还没有完全封城。写的时候主要想奥地利!还想到资本经济。为啥写中文?想想吧,资本经济哪里最厉害?是先写了中文,一开始都知道说法不完美。问题显出来,也许是口语吧,但是中国有口语诗人这样写诗吗?一开始感觉到这个,还是没办法。以后图雅说就这样写才能写得出来。五月份我们维也纳家有从德国来的客人,德国著名犹太女作家 Esther Dischereit。她曾经在维也纳当教授,2015年跟其他不同大学的教授邀请伊沙、郑晓琼来奥地利。Esther 住在我们家里,杜鹃和我有机会听到她念出诗,就是她十几年前或者更早写的,音乐性非常强的,都是比较短的,说到孩子长大的诗歌。都是她随时能背的。非常好!然后有一天我也给她念自己的最新的作品,《本来的问题》,先读了德语版。她马上说像一个老人家活到老才能说出的判断,有一点讽刺。就是讽刺,谁有资格说整个世界本来的问题?我觉得也许自己从中文翻译成德语不够好,不能翻译出本来的不知道怎么说话的问题。英语 original problems, 德语 Probleme, die da waren。这个很口语,翻译出来了口语的日常语言的味道。只是没足够翻译出来原文显出的尴尬。而且毕竟我和 Esther 是完全不同的诗人,虽然都关心政治,尤其是当面的社会问题。她因为有这个关心,而且是国际的,开放的关心,才接触到中国的诗歌。
伊沙最近只可以随便说西方的问题,其他的不能随便说了,比以前严格的多。结果开始自己说别人批评清零措施就是诗怨,要不是诗冤吗?好像是前者。别人可以写当面的问题,伊沙不能写了?受不了!必须可以怪其他的诗人。因为伊沙就是比较直接反应当面社会情况的诗人。就是写涉及到政治的诗人,中国的和国际的现象都有。这两年世界很多地方有非常大的严重的问题。像 Esther 或像伊沙的诗人,就是虽然背景完全不同,但都是关心社会和政治的诗人,在这样的时代必须有反应。那么如果因为各种原因很多反应都是限制的,怎么办?本来已经写比较间接的诗人还比较容易。可以说不一定需要写铁链女。只是因为伊沙以前写社会问题写了非常成功,所以现在不写有点尴尬。我当外国人也许最容易,完全不公平。
铁链女
维马丁
铁链女
在哪里?
解封了吗?
有没有阳性?
铁链女
永远
隔离
吗?
镇压女人
奥地利也有
有过极大极荒谬的案子
被镇压的女人
消失了吗?
至少
没人禁止你
谈这件事
2022.5
就是不公平!不过我这个老外男人写出来这样的中文诗,有人想读吗?也许不可以发表,除了网上之外。春树喜欢,春树给肯定很难得!就是因为她已经写了很厉害。她的诗可以发表吗?这个题目除了网上也许都不能发表。不过春树有她的小说。写诗重要,一直写诗,但还是主要因为写小说才得到大家都知道的著名作家的位置。
寻找
春树
有一个人被抓走了
下落不明
我们寻找她
就像寻找森林里消失的小鹿
有一个人下落不明
总会还在哪里藏着
我们关注她
就像关注清晨的露水
开放的花朵
她被谁摘走了呢?
叶子上的露水
也要被阳光晒干了
她们在哪里呢?
还有人一直在寻找她们呢
她们的名字是什么呢?
她们自己知道
造物主也知道
2022,4,16
非常厉害!但愿伊沙可以在新诗典推荐这样的诗!以前好像可以,有时候。反正觉得,写了这首诗,春树都不用写战争。已经写了世界级的非常难得的杰作。
好,现在写到哪里?喊口号,湘莲子说喊口号好,友谊万岁!是的,玩玩岁岁,岁岁平安。
谢谢大家!谢谢伊沙,谢谢徐江,谢谢所有的提到和没有提到的朋友!
2022.6.14 – 2022.6.15